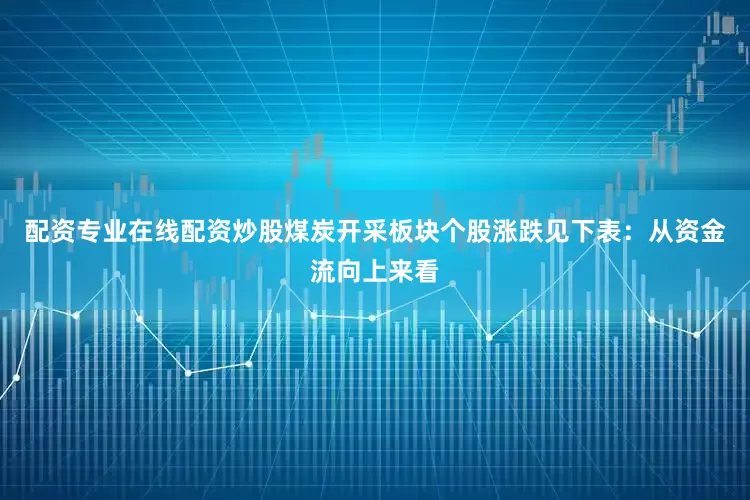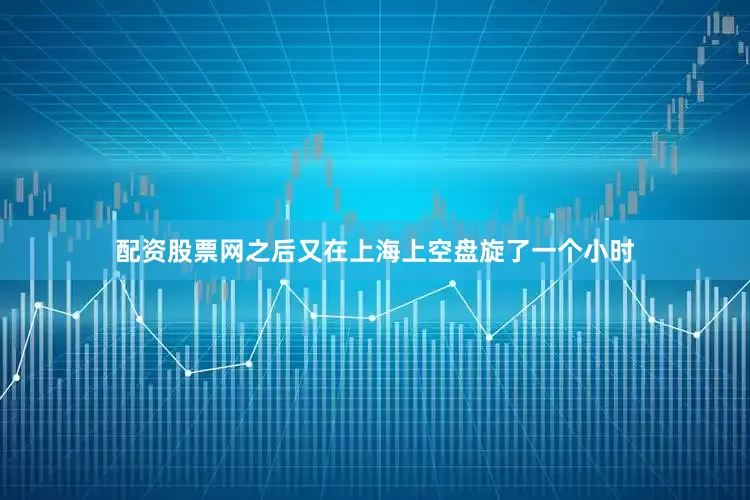
“我爱上了凤,也爱上了龙,了解和热爱中国龙,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凤。”这是沙博理在自传《我的中国》里,深情告白已故妻子的文字。沙博理,这位来自中国的犹太人翻译家,心中最爱的“凤”,正是他一生挚爱、剧作家封季壬,艺名凤子。
五十年的相伴相守,是凤子拉着沙博理走进了中国人的世界,是她让他找到了归属感,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。1947年4月1日的上海,凤子那时正伏案创作她的小说《画像》,故事中的女主角如同她自己,挣脱了束缚她的家庭枷锁,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。
这篇小说也像是凤子的画像,她那段失败的婚姻成为了创作的源泉。十年前,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凤子,凭借出演曹禺的经典剧作《雷雨》和《日出》而成名,那时她吸引了历史学者孙毓棠的爱慕。然而,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,孙毓棠希望她回归家庭,而凤子则热衷于戏剧和抗战。当她决然离开,婚姻便走到了尽头。
展开剩余81%尽管如此,凤子并不后悔。在重庆,她的演技得到了朱自清和郭沫若的高度评价,那时她感到自己前途光明,眼中闪烁着“如烈日般的坚定和明澈”。就在她全身心投入创作时,小屋的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。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青年,带着一口不太标准的中文说:“我找凤子女士。”那时,凤子记起远在耶鲁大学的老友杨云慧曾提过,沙博理是她的美国同学,计划来中国学中文,希望她能介绍一下。
沙博理一见面便向凤子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他曾是一名律师,在珍珠港事件后参军,战后进入大学学习中文,并受中国同学的建议来到中国。他的亲切和真诚令凤子感到十分亲近,而沙博理眼中,这位身穿旗袍、微施粉黛的东方女子,面容如同镀了金的百合花,美丽而又清新动人。
当天离开时,沙博理内心愉快,期待着下一次见面的机会。刚到上海的沙博理并没有工作,生活拮据。正当此时,有人提出资助他的条件——让他和那人女儿结婚,帮助其女儿成为美国公民,之后再离婚。对此,沙博理礼貌地婉拒了。凤子得知后,十分赞赏他的立场,并鼓励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工作。沙博理最终找到了律师的工作,两人开始更加密切地交往。
随着时间推移,沙博理的绅士风度和温文尔雅打动了凤子。他们一起看话剧,读小说,品茗龙井,游览城隍庙,成为了彼此最亲密的朋友。凤子也引领沙博理接触了很多文化名人,他们经常讨论解放区的消息,这使得沙博理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不知不觉中,沙博理不仅深深爱上了中国这条象征着力量的龙,也渐渐爱上了这位充满朝气和魅力的凤子。1948年,沙博理向凤子求婚,凤子的内心如被石子击水,涟漪层层荡起。尽管她对沙博理充满信任,但这毕竟是一场跨国婚姻,她感到有些犹豫。
然而,一件事彻底打消了凤子的疑虑。那天,凤子从香港乘飞机回上海,途中遭遇大雨,飞机不得不绕道南京,之后又在上海上空盘旋了一个小时。最终,凤子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时,却看到沙博理正焦急地打电话给机场。当他看到凤子安然无恙地站在眼前时,他激动得一把将她抱住,泪水止不住地涌出。
爱情的力量让凤子下定决心。1948年5月16日,凤子与沙博理在上海举行了婚礼。当时,凤子36岁,沙博理33岁。婚后的沙博理无微不至地照顾凤子,哪怕她拍戏拍到深夜,他总是准时出现在片场接她回家。凤子所编辑的杂志因经费紧张,沙博理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收入提供支持。作为外籍人士,他还悄悄保护了多位地下党员。
新中国的诞生在即,在这片爱的土地上,凤子和沙博理一起朝着北京进发,奔向未来。1950年,他们的女儿亚美出生,名字象征着亚洲和美洲的结合。
定居北京后,凤子的工作越来越繁忙,而沙博理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,开始翻译长篇小说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。最终,凤子联系了周恩来总理,建议沙博理进入对外联络局担任英文翻译。
就在沙博理刚刚开始适应中国的新生活时,朝鲜战争爆发,凤子作为慰问团成员之一,前往朝鲜。那次穿越山谷时,敌机的扫射和爆炸声骤然响起,一名相声演员当场牺牲,凤子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愤怒。她目睹了美国军队的暴行,而这些暴行让她对沙博理——一个美国人——产生了痛苦的情感冲突。
尽管沙博理一向主张和平,且为美国媒体写文章批判美帝的侵略,但凤子仍然深感内心的冲突无法调和。回到北京后,她对沙博理变得冷漠,外界甚至注意到她的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她向朋友诉说内心的矛盾,最终选择离开沙博理,远赴江西参加土改。
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凤子逐渐意识到,沙博理一直深爱着她和他们的家庭,更爱新中国。她冷静后回到了北京,并重新投入到工作中。在此期间,沙博理除了继续翻译,还在凤子的指导下参演了几部电影,开始在银幕上留下一些传奇的身影。
岁月流逝,沙博理的中国情结愈发深厚,他爱上了中国的茶文化,喜欢穿上布鞋、对襟棉袄,甚至能流利地讲普通话。1963年,沙博理正式加入中国国籍,并誓言与凤子一起度过余生。即使在动荡的岁月中,凤子被关押时,沙博理依然每日前去探望,支持她。
随着岁月的推移,他们的爱情越加深厚。沙博理的翻译事业进入巅峰,《水浒传》成为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,所有的翻译作品都凝结着凤子的智慧。无论是从香港到以色列,还是在家中与凤子共同度过的日子里,他们相互扶持,笑容如初。
当金婚的日子临近时,凤子写下了充满期许的文章《迎接金婚》。她满怀希望,期待着和沙博理一起享受宁静、愉悦的余生。然而,命运并未眷顾他们。凤子在不久后因病离世,沙博理在她的葬礼上,泪眼朦胧,他把她的作品视作永恒的纪念。
2011年,沙博理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得“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”。他在领奖时说:“我希望我的根永远留在中国。”四年后,沙博理安详辞世,他的生命与凤子的爱如同永不褪色的印记,历久弥新。
发布于:天津市短线配资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